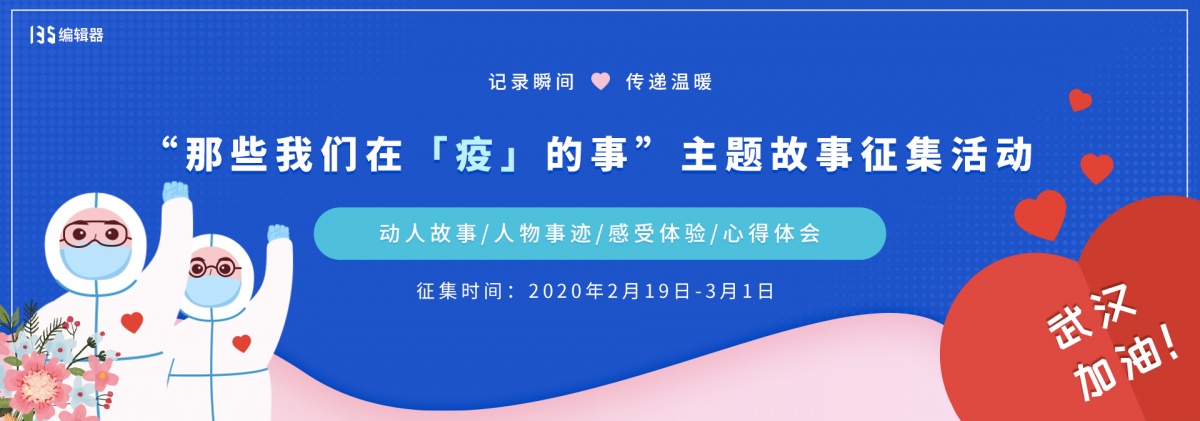防疫期間的愛情(小小說)
“哎�����,小段����,你看�,2單元103號(hào)的老婆子又出來了��!”
老高拿下嘴里叼著的利群煙����,把剛添滿的一大杯水?dāng)R在執(zhí)勤桌上�����,拍了一下我的左肩膀,努著嘴示意我看掛著“舌尖尖牛肉面”門牌的那邊門洞����。
“果然啊����,這次又不知說啥理由�!”我停下正在撥弄火盆的鉗子��,回歸到桌子前,端端正正坐好�����,進(jìn)入候命狀態(tài)���,整理了一下被風(fēng)弄亂的出入人員登記表、來訪人員登記表和電子測(cè)溫儀器���。
老高咂了一下已經(jīng)燃到過濾嘴的煙蒂���,把海綿嘴丟到火盆里,胡子拉碴的臉嚴(yán)肅起來�,站立得像個(gè)將軍�����。
那老人家已經(jīng)出了檢測(cè)點(diǎn)管轄樓的門洞�����,腳步不緊不慢���,朝警戒線走過來。瘦弱的身體外面裹著印著蘭花花的黑棉衣�����,頭上戴上了圓形禮帽����,藍(lán)口罩遮住了大半個(gè)臉���,只露出了一對(duì)犀利的眼睛���。
“哎�����,你今天出第幾次門了�?”老高的話語充滿質(zhì)問味。
那老人家沒有搭話����,繼續(xù)往前走����,但我感覺臉拉得老長(zhǎng)老長(zhǎng)了����。
“哎����,哎,問你話呢����!整個(gè)樓里86戶人家都是每天一人出門買一次吃食���,你咋不聽話.。我沒記錯(cuò)的話�,今天第三次了吧�����!”老高的臉由紅變黑了�,語氣硬得像吃了刺猬�。
“咋了�,你管犯人哪�����!”禮帽下的藍(lán)口罩里噴出“火”來了�!
“這是制度�,你昨天出去了五次���。領(lǐng)導(dǎo)查看記錄冊(cè)�,把我們訓(xùn)了個(gè)狗血噴頭!”老高聲音提高了八度�����。
“這樣對(duì)待群眾�����,領(lǐng)導(dǎo)不訓(xùn)你才怪呢��!”
老高氣得要發(fā)作���。
我看火藥味越濃烈了����,一把拉他坐下。
我站起來����,手里拿著“槍”�,邊問話邊把“槍”伸到老人家的額頭����。
“34.2度�����!”我看了一下測(cè)溫器�����,又在自己的額頭瞄了一下��,再看——33.9度�����。心里想���,這玩意看起來高科技,樣子貨�!氣溫跳崖了,它也就跳崖了。
“36度2�����,出入證不用看了�,您的住址我都背下來了!”我把聲音降了36個(gè)分貝�,“老人家這次出去買什么呀�?”
“買蔥——”老人家已經(jīng)轉(zhuǎn)過身,可能聽見我聲音和氣����,側(cè)過頭來說了2個(gè)字�!
老高又點(diǎn)上一支煙����,看著她漸去的身影�����,憤憤不平�,又像喃喃自語:“這老不死的����,整得咱們挨訓(xùn)!昨天買了蔥���,今天又去買蔥,她整天就吃蔥過活呀��!”
登記完信息�,抬頭看看天,陰得重的����。我把大衣裹緊���,進(jìn)了帳篷,圍在火爐邊烤手���。昨夜大風(fēng),今早氣溫快零下了�,這檢測(cè)點(diǎn)的火爐又是有氣無力�,怎么都燒不旺�。
看到帳篷外側(cè)的值班點(diǎn)編號(hào)單,我不由得笑了�,笑得老高莫名其妙。
老高是我單位的公益崗職工���,50多了�,平日管理單位衛(wèi)生����,人倒是心眼好�����,腳勤手快,就是說話大嗓門�����,讓人覺得老是在訓(xùn)人。這次抽調(diào)防疫值班他和我一組����,每?jī)商煲粨Q班��。
“老高�,你知道《二六七號(hào)牢房》嗎�?”我看看那藍(lán)底紅字的“267”三個(gè)數(shù)字���,被風(fēng)帶動(dòng),一晃一晃的�����。
“啥267號(hào)�����?奧——你是說咱這值班點(diǎn)的編號(hào)���!”回頭看了看帳篷內(nèi)的面積,四方四正��,邊長(zhǎng)大約就是七尺!就想起來伏契克大作里最經(jīng)典的話句“從門口到窗戶七步�,從窗戶到門口七步”�。簡(jiǎn)單地給老高說了文章情節(jié)。并打趣地說:
“歷史總有驚人的相同!可惜呀����,咱們?nèi)侨鲩_這么多人來檢測(cè),挨餓受凍的���,點(diǎn)燈熬油的,還不是為了整個(gè)小城的安全�����,可是有的人就是沒危機(jī)意識(shí)�����,老不聽話么��!”
老高對(duì)文學(xué)不感興趣����,掐滅煙頭����,踩在腳下。突然問我��,小段你多大了,哪里畢業(yè)的�����,工作幾年了�。我說了����,又問干啥呀,查戶口呀��!老高饒有興趣地說����,不錯(cuò)呀����,名牌大學(xué)畢業(yè)�,29歲,又年輕又帥氣的����。對(duì)象找下了嗎��?
“找個(gè)辣辣�!在這個(gè)小城里�,像我這年齡,孩子都上幼兒園了�,典型的剩余產(chǎn)品么!”我感嘆一聲����。
“你眼頭高得來么��?”老高進(jìn)一步套取信息�����。
“高啥里�����,談了幾個(gè)��,人都能彼此看上��,涉及關(guān)鍵問題就崩了���!”
“啥問題啊!不會(huì)是生理問題吧����!”老高一臉壞笑。
我摘下眼鏡��,用紙巾把鏡片上的霧氣擦了擦�。“虧你還撮合婚事呢,沒聽過‘有樓有車職位還要帶長(zhǎng)�����,父母公職退休是提錢銀行’的嫁人標(biāo)準(zhǔn)嗎?我老爸老媽是農(nóng)民�,弟弟妹妹在上大學(xué),這標(biāo)準(zhǔn)一個(gè)都不符合么���!”我笑了笑說。
“這倒是事實(shí)啊�,這幾年我也說成了幾對(duì)����,確實(shí)這樣�。農(nóng)村里結(jié)婚第一條件就是城里買房,彩禮高得降不下來么����!”老高又點(diǎn)起煙,遞給我一支�,我推了。
剛要起來給火爐上夾碳����,聽見帳篷外有人�,趕緊出去�。
眼前站著兩人����。一個(gè)高個(gè)子的年輕女的攙著一個(gè)老年人,都戴著口罩��,包得嚴(yán)嚴(yán)實(shí)實(shí)�。但老年人能看出來���,是剛出去的那位老人家��。
“老人家���,這么快就回來了啊�!”我把“槍”對(duì)準(zhǔn)她的額頭�。她退后了一點(diǎn)�����,“別量了��,哄我老瓜子里��,34度還說是36度�,裝啥樣子里��!”我愣住了���,天呀,老眼睛那么厲害呀��,比我戴著眼鏡還看的清����。
“你們兩個(gè)站開一點(diǎn),保持2米距離��,不要挨那么緊���!”老高發(fā)話了���。
“誰前面罵我媽了��!”那年輕女的發(fā)問���,聲音倒是好聽�����,就是不太柔和����。
“啊�,奧�,沒人罵呀��!”我看看老高��!老高頭頂貧瘠的土地上僅有的幾叢草被陰冷的風(fēng)刮得倒立起來了�,臉由黑變紅了�����。
“干啥呀����,還請(qǐng)救兵來還大鬧法場(chǎng)呀!一天能出五六次��,一會(huì)買蔥����,一會(huì)買蒜,一會(huì)買面條���,一會(huì)買豆腐����,貓拉屎一樣出出進(jìn)進(jìn)����,害得我們……”正在填寫信息表的我,忽然覺得天降大雨��,全部下到我的頭上了����!眼睛被沖洗得一片模糊�,右半邊臉上冰涼冰涼的���,水滴吧嗒吧嗒從下巴上掉下來�����,左手袖筒里濕浸浸的�����。
我激靈一下站起來���,摘下眼鏡,看到那年輕女的手里握著紙杯��,一臉驚慌���,支支吾吾地道歉:“對(duì)不起,對(duì)不起����,不是你啊��!誰讓他說我媽貓拉屎……”
老高退后一步站著�����,嘴里在放炮還擊����。
我拉了老高一下���,讓他別說,快找毛巾來�����。
那女的掏出手提包里的紙巾�,抽出一沓遞給我,又慌忙地幫我擦頭發(fā)上���、衣服上的水珠。嘴里面說著“我也在值班�����,兩天一輪�。我媽年齡大了���,哥哥在外地�,家里馬捅壞了�,叫不來修理的�����。每天出去是上公廁……”
不知什么時(shí)候,她的口罩一側(cè)掉了��。我看到了一張白皙又俊美的臉��,黑葡萄一般的大眼睛里洋溢著那么多的著急愧疚��。一種清香的氣息散發(fā)開來�,包圍了我�,仿佛春天的所有花兒已經(jīng)開了�。
一個(gè)月后,疫情全面狙擊成功����。267號(hào)帳篷被我們用雙手搭建�����,又被我們拆除。
我站在編號(hào)牌前合影��,做個(gè)紀(jì)念——這地方竟然有緣���。
……
半年后�,我陪著新婚的媳婦回娘家��。
在穿過舌尖尖牛肉面的門牌前��,忽然閃現(xiàn)出了半年前在267號(hào)檢測(cè)點(diǎn)執(zhí)勤的畫面來���。不由得停下步子����,把緊握著的媳婦的手順到眼前����,仔細(xì)地端詳著�。
媳婦俊美的臉上滿是疑惑��,嗔怪著:“快走�����!我媽做了好菜等著呢�����!你這看手相啊,瓜不癡癡的����,還沒看夠!”
“沒想到你這手的命中率那么啊����,投球高手?����?�!怪不得我們?nèi)值娜硕颊f�����,別人的愛情火焰是被冷水澆滅的�,而我的愛情是被冷水點(diǎn)燃的!”我開心地笑了�����。
“才不是呢��,本來是朝那個(gè)氣人的老高的�,沒想到你接招了���!”媳婦順勢(shì)翻看我的手,“我看看���,你這手相也不錯(cuò)嘛�����,怪不得我媽不要樓房不要車,就把我就嫁給你了�。原來你這手看來除過脾氣好,還能修馬桶?���?���!”說完,咯咯咯地笑著跑前面去了���!
“好啊,你敢笑我��!”我拎起東西追進(jìn)去�����。
楊紅林:教師����。70后,甘肅涇川人